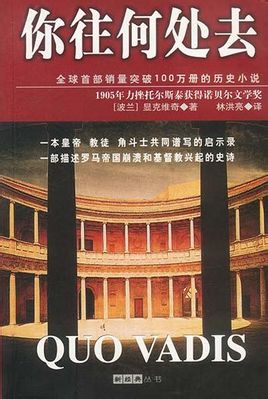艾蒿绿了
一
清明过后,村子南边的水渠边上,杂生的艾蒿渐渐绿了,将水渠围成一片葱葱郁郁。一场雨后,一簇簇密密实实摊开的艾叶,水洗了一样碧绿清透,在清晨的凉风里,轻轻摇曳起舞,叶面上的小水珠在攒动中滚落下来。
秀兰起得早,她是在去自留地点瓜种豆时看到的。那一瞬,这个乡村女人眼底里,一抹藏不住的惊讶和惊喜。接着,眼窝深处,也有一丝丝的怅然和叹息,不由自主从唇角溢出来。
怎能不伤心呢?她的小女儿乖侠死在天寒地冻的腊八时节,就埋在水渠尽头的北坡上。可怜的乖侠,一从自己肚子里出来,就落下先天心脏病,不敢生气,不敢兴奋,稍微不慎,就会直挺挺晕厥过去,搞得村里的孩子们都不敢接近她,和她玩耍,恐闯了大祸。乖侠很懂事,伙伴们疯玩沙包或跳九成宫时,她总在站在一边安静看,脸上的笑也浅浅的,淡淡的。
转眼,该上学了,同伴们一个个背着书包去了学校,秀兰的乖侠,只能坐在自家的门槛上,眼巴巴瞅着,甚至乘家里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跑到学校,踮着脚尖,趴在窗台上睁大眼睛一边看,一边跟着老师念拼音,读汉字,数指头。声音小小的,又怯生生的,神情却专注得忘了自己的娘早已站在身后多时了。等她转过身子时,看到娘满脸的疼惜和泪水。
乖侠被秀兰送进了学校。当然,也费了很多周折,是秀兰硬逼着自己男人去求校长和村长,说了很多好话,还签了一分协议,协议里说,乖侠在学校因自己原因造成的一切意外,与学校无关。秀兰的男人,大字不识几个,在纸上签字和按手印时,那双粗糙的手,颤抖得放不下,而这个村野男人,却因女儿可以识文断字,乐得眼睛迷成一条缝。
乖侠上学了。书包是娘新用蓝色咔叽布做的,上面绣了一丛丛兰花艾草。她念书很用功。上学和放学路上,都在背书;课间休息,伙伴们在教室里你追我赶,嬉闹玩耍,她在座位上,安静看着,貌似开心的样子。算是平平安安上到小学三年级了。一次,她看着同伴蹲在地上玩抓石子,按捺不住,也小心翼翼玩上了。玩到尽兴处,上课铃响了,大家一窝蜂似的往教室跑,她也跟着一路小跑,可还是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一口气没喘上来,嘴脸乌青不省人事,没熬过半夜就咽气了!秀兰难过得捶胸捣足问上天为何不带走她而要带走她如花骨朵一样的女儿!眼泪哭干了,她很平静地给女儿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辫子上扎了两朵用红头绳挽起来的蝴蝶结,一张席子卷了她,拉到村子沟边的土壕里埋了。此后,秀兰忙完农活后,总忘不了去那处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土堆边坐坐,给坟头放一把红枣、几颗水果糖或者五六个核桃。
其实,四月的乡下,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一簇簇,一疙瘩的艾蒿,早已在春意盎然中嫩绿青翠得让人心生几分欢喜出来。
往年这个时候,秀兰必然要蒸艾蒿菜团的,女儿乖侠一直喜欢吃,怎能忘呢?她依旧蒸好嫩艾蒿菜团,还专门调成女儿爱吃的酸辣味,掰成小块,撒在乱草堆里。奇怪的是,一个春天里,小小的坟茔四周,长出满满一地的艾蒿,一日比一日茂盛。
二
小女儿死后,秀兰相继添了两个儿子,她从早到晚不停忙乱着,暂且淡忘了对小女儿乖侠的殷殷思念。过了几年,大女儿乖丽和二女儿乖红相继出嫁,秀兰的身边,是手脚勤快的男人和两个年少的儿子。日子平淡着,也平静着,像一面湖水。
联产责任制后,秀兰家分到五亩田地,她和男人起早贪黑,手脚不闲地在地里刨着,日子也渐渐好起来。磨面时,秀兰总要专门收一袋子细面,蒸出的馍,白生酥软,两个儿子狼吞虎咽吃,吃得打着响嗝,却满脸堆笑。偶尔,秀兰和男人拉着架子车去镇上赶集,顺便买些干货炒菜,换上几斤大米,割上二斤猪肉,打上二两小酒。春夏交替时,秀兰也会一家挨着一家服装摊位转,为大狗二狗买回来新衣裳和新鞋子。中午时分,秀兰家的院子里,飘来西红柿炒鸡蛋,肉丝炒蒜苔的浓浓香味。她男人坐在石凳上,滋溜一声押着小酒,酣畅淋漓,大狗二狗迫不及待从厢房里拿出新衣裳和新鞋子,各自炫耀,各自吹捧,嬉闹声从又窄又深的老院子里,满溢出来。
秀兰一个村野之妇,还有什么比日图三餐夜图一眠的安稳日子更让人安慰呢?她满足极了。她甚至想着,若这般长久下去,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每天晚上,秀兰拾掇完屋子的活,都会打坐在灯下侍弄针线活。有时是爷弎的的鞋底子,有时是满地跑的外孙女妞妞的新棉袄。秀兰的男人干了一天活也累了,正在炕头歇脚。他喜欢抽旱烟,烟斗里一撮烟丝点燃后忽明忽暗,男人抽得很滋润,满嘴砸吧着,吸得过猛时,也会被呛上几口,却依旧说,解乏,舒坦。
乡村的夜很安静,整个村子仿佛睡着了。偶尔,邻家的门吱呀一声开了,门口的狗立即蹿出来,叫几声,惹得满村子的狗都叫了起来,之后,又是很深的寂静。
转眼之间,大狗和二狗,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农家人的日子像车轮,滚碾着一个个日头从东边出来,西边落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迭着,繁衍着,轮回着。
一天,秀兰的男人下地回来,浑身疼痛。疼得按捺不住时,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落下来,嘴唇也咬出很深一圈血印子来。秀兰吓坏了,赶紧陪着男人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男人患上严重的肝病,已是晚期。
秀兰看着化验单,满脸疑问:自己男人的身体好得跟一头牛似的,咋会呢?
大夫说,这病,不是一天两天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已经很严重了,熬不过两年。
听到这一消息,秀兰犹如挨了当头一棒,她吓傻了,半天回不神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咚”的一声,双膝跪地一口一声地求着:大夫,求你救救他,就是砸锅卖铁,吃糠咽菜,我男人不能死。
大夫赶紧扶起她,用平静的口气告诉他,不要花冤枉钱了,回去吧,尽量减少病人的疼痛。
那一瞬,秀兰在大夫眼里读出了遗憾,她几乎绝望地将男人拉回家。
三
男人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止疼药抓把把吃,杜冷丁一盒盒打。这些止疼药,暂时止住了男人的疼痛,止不住的,却是西药带来的副作用在与日俱增。尤其是她的男人,持续拉肚子好几个月了,身体眼看扛不住了。终于一日,这个曾一口气干掉一老碗手擀面的男人,甚至连一碗面糊糊都喝得很艰难,秀兰难过的背过头去。
秀兰熬不住了,坐在女儿的坟头大哭了一场。她的身边,暮春的风儿吹得正熏暖,风过处,一股淡淡的草香夹杂着草药的味道扑入她的鼻翼间,那是艾蒿的香气!她猛然想起,这东西可以止泻,好像还可以止疼,何不试试呢?
这样想时,秀兰用手扯了一把,急急匆匆拿回去晾干,揉碎碾成粉墨,用酒点着,每天轻轻擦男人的肝部,加上按摩,男人的疼痛真的减轻了,胃口也渐渐好起来,脸上有一丝丝的红润。
那一瞬,秀兰喜极而泣,她的脸上,热泪滚滚。
女儿坟头的艾蒿一茬茬被她拔掉,又茬茬长起来。一日,她索性连根挖了一撮撮栽倒后院里,不曾想,不出半个月,那一撮艾蒿,根茎扎稳了,攒着劲猛涨,几场雨后,已经蔓延了好一大片,葱葱郁郁,惹得满后院子都是艾蒿的香气。
夏至后,艾蒿长得半人高,碧绿的叶子和茎杆上蒙了层白绒毛,沾满清澈的露珠,偶尔还开出一小簇淡黄色的花儿,细碎而素净。待到立秋时,艾蒿长老了,叶子厚实肥大,药味更浓,效果更好,秀兰自然满心欢喜。她赶在艾蒿叶子枯萎之前,挥舞着镰刀将铺成一地的艾蒿割干净,阴凉处风干,碾成粉末,塑料袋捆扎结实,装在密封好的瓶子里,等冬天给男人继续用。
秀兰又赶在霜降之前,到镇上的供销社买了厚厚的塑料纸,将艾蒿的根,围了个严严实实。
那个冬天,冷得出奇,寒流一次次袭击村子,村子里的老老少少一茬茬的感冒、咳嗽或发烧,但秀兰的男人大抵坚持用了艾蒿的缘故,他虚弱的身子竟然扛过了整个风雪弥散的冬日。
惊蛰过后,春天来临了,后院的艾蒿根在春风的吹拂下,一点点露出鹅黄的幼芽。勤快的秀兰,经常给浇水松土,那幼芽,竟然生得绿油油的。
春天的艾蒿,嫩绿轻柔,苦味也少了很多。秀兰在蒸馍时,到后院摘上几把,择洗干净,揉进面里,或洒上椒盐,或拌上糖,捏成大约茶杯口大小、圆圆的、偏偏的,一个个放进笼锅里大火蒸熟,颜色碧绿绿的,油亮亮的。大狗和二狗尤其喜欢吃秀兰在热锅里煎炕艾蒿馍,油煎的艾蒿馍油绿滋糯,特别清香甜美,面上一层脆脆的,味道好极了。院子里,爷弎一边大口吃,一边谈笑风生,院子里,又恢复了以前朗朗的笑声。
恰巧,在灶台下烧火的秀兰起身翻转锅里的艾蒿饼,她看到这一幕,眼眶发酸。随之,热辣的泪水从眼角溢出来。
一盘艾蒿饼子烤好了,秀兰唤二狗来厨房端。她用手撩起散落在额头的一缕乱发,靠着门框,也深深笑了。
四
秀兰的男人最终撒手人寰,比医生的宣判时日多活了一年。
这个男人,走在艾蒿疯长的时节。
走的前一天,吃完早饭,天阴沉沉的,连空气也湿漉漉一片,接着,起风了,下雨了。秀兰在厨房里正收拾碗筷,二狗进来说:娘,爹好像有话要说。
秀兰解下围裙走进厢房,她的男人正斜靠在炕头,有亮光从窗户里透进来。他的脸上虽然有些苍白,却很平静。此时,他已预感到自己生命就像一盏耗尽的油灯,只需一丝风,就熄灭了。看着眼前的大狗和二狗,虽未顶门立户,但毕竟和门前的小白杨一样长起来了,还好,可以帮着秀兰锄地,拔草,秋收时,大狗可以驾辕帮着秀兰拉玉米棒子和播种时,这娘弎,在世上应该也能相依为命,共同撑起一片天吧?这是他临走前颇感安慰的。但他知道,这都是秀兰的功劳。自己要走了,一定要让孩子们懂得。
他把哥俩叫到炕头前,叫他们跪下给秀兰连磕三个响头,让他们记住秀兰的好,秀兰的不易;还叮咛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孝敬自己的娘,替自己照顾好秀兰。
显然,男人在和自己一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辛苦操劳了半辈子的女人做最后的告别。门口屋檐下,已经落巢多年的麻雀,叽叽喳喳叫得正欢。秀兰曾经说,他们两口就是那同病相怜的麻雀,他喜欢听秀兰这样说。
如今,再看一眼身边的女人,除了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依然似一汪清泉外,脸上被毒辣辣的日头晒出很多黄斑,额头上多了一道道细密的皱纹,尤其是那双纤细柔软的手磨出了很多茧子来,很粗糙。这个七尺汉子,他的眼里,有深情的回眸,也有深重的怅然。他的手,紧紧拉着秀兰的手,疼惜和痛楚,在眉间反反复复纠缠,他用微弱的声音,轻轻告诉秀兰:“嫁给我们家,你受苦了,不过,下辈子,我还想娶你做老婆,让你过上好日子,行不?”
最后,男人告诉秀兰,给自己的坟头栽上一撮艾蒿,心里惦记她的时候,看见绿油油的艾蒿,就等于看见了秀兰。
秀兰脸上挂满了泪水,她朝自己的男人,使劲点了点头。
说完这些,男人闭上了眼睛,咽下最后一口气。
三天后,村子南面向阳的土坡上,杂草丛生的坟地里,垒砌出一个新土堆,那里,长眠着秀兰的男人。
秀兰带着大狗和二狗,从后院里铲下满满一架车的艾蒿,将它们围着坟头,栽得密密麻麻。还有几棵长青松柏,一起摇曳在风中。
秀兰坐在坟头,自言自语:他爹,再过些时日,这些艾蒿会扎下根,会抽出新叶,会罩满你的坟头,蛇和蜈蚣自然不会钻进去骚扰你了。还有,艾蒿长起来了,那味道也一定会从地上钻进地下,钻进你的心窝里。
暮色渐起,秀兰顺着半坡上望过去。她仿若看见,不久,会有成片的艾蒿,绿盈盈地摊开来,像自己和男人永远葱茏茂盛的情分
远处的村子里,一缕炊烟正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来,飘向远处。
秀兰领着大狗和二狗,向着村子走去。他们身后,艾蒿的香气,正浓。